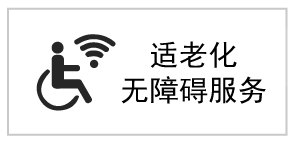省报看阳西:古堡流芳

横山村泰安堡红色教育基地。

定安堡正门。

位于塘口圩的周安堡。任浩沿 摄

位于塘口河最上游的镇安堡。

古堡以前曾改建用作学校,供村民子弟读书。图为泰安堡。
8月17日,一场大雨突降阳江,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都未停。18日,在我赶去塘口看古堡的路上,这雨还是时大时小、时急时缓。雨大的时候,滴滴答答地敲在车窗上;小的时候,飘飘洒洒散落在路两旁的田野上、竹林间。看着淅淅沥沥的雨点,我不由得摇下车窗,伸出双手感受那丝清凉,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山野、天地进行一场的对话。
我去过塘口古堡群,不止一次。
车子进入塘口境内,山丘明显多了起来,道路也变得高低起伏,一座座山从窗边闪过。好奇心驱使,我用手机搜索了一番得知,原来横亘在广东西部的云雾大山绵延几百里,跨越阳西、阳春、恩平、电白多地,而塘口就坐落在云雾大山的西山山脉南麓。相传,明末清初,在塘口周边的深山老林中,有多股顽匪踞山结寨,终年打家劫舍、窜扰民宅、掳人掠货,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抵挡匪患,当地百姓纷纷以姓氏宗族为单位,竭资尽力筑起高墙堡垒。
据资料记载,多年来塘口先后建起大大小小、风格迥异的古堡,至今大部分的古堡依然屹立在塘口河畔。沿塘口河顺流而下,依次是桐油姚姓的竹松书室、邓姓的镇安堡、上垌黄姓的定安堡、塘口圩陈姓的周安堡、横山刘姓的泰安堡,以及塘口河支流高河北岸刘姓的永安堡等。单从古堡名字上看,就可看出建设者们的良苦用心和祈望国泰民安的愿望。这些古堡在地势布局上遥相呼应,过去一旦发生匪情,住在古堡里的人们就会互相支援,共同抗击恶匪,久而久之,古堡便成为保护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安全岛”。
1
我们的第一站,是塘口河最上游的镇安堡。镇安堡位于桐油村内,坐落在一片绿野平畴中,四周被庄稼、野草和小树包围着。迈过泥泞的田间小路,我小心翼翼地走近落寞而苍凉的古堡,生怕粗重的脚步声惊醒它。
据了解,镇安堡由邓氏家族捐资合建而成,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这200年间,堡里的邓氏族人陆陆续续迁了出去,昔日热闹的院子也慢慢沉寂了下来。现在,堡内只剩有三四间房子还有人居住,偶尔可以看到有人开门出来,又迅速离开。房门在他背后“吱呀”一声,又合闭上了。缺少人气的院子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草,一簇簇地从墙脚爬上墙头,迎风吹拂着。
同在桐油村的还有一座古堡,那就是松竹书室,这是几座古堡中规模最小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松竹书室四周筑着高大厚实的堡墙,其他古堡拥有的设施和防御功能它也一样不缺。只是如今,在日晒雨淋中松竹书室墙崩房塌,断砖瓦砾遍地,主体建筑破损得非常严重,大片的荆藤爬在倒塌的残垣断壁上,严实覆盖着。见此景我也只是在门口踌躇了一下,便离开了。
在古堡群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周安堡。近几年开始,周安堡被用作当地政府办公楼,而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随队前来调研工作,所以周安堡也是我最熟悉的塘口古堡。我常利用工作之余在堡里四处溜达,随手触摸着这200多年的斑驳时光,也因此堡里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条过道的气息我都很熟悉。据悉,周安堡占地3万平方米,相当于5个足球场的大小。堡墙厚达1.2米、高7米,顶端还建有2.4米宽的隐蔽通道(马路),便于运动车仔炮作战。
昔日,周安堡是陈氏族人的活动中心。堡内建有太祖祠、永贞祠、芳林祠、竹林祠、凤山祠等5座祠堂,还设有炮楼,墙体也设有多处炮眼。如今,虽然其四周厚实的城墙基本已被削平,但堡内的房间大都被保存了下来,并得到修缮完善,一直沿用至今。
2
赶到横山泰安堡的时候,雨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走进横山村我看到,近处几间房屋掩映在绿树丛中,黄皮、龙眼、荔枝等果树在屋前屋后种着,一串串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屋檐下,一条黑狗正呼呼地睡着午觉,待我们走近时,它也只是微微睁眼瞪了一下我们,随即伸了个懒腰继续睡去。远处,青黛色的大山层峦叠嶂,大块白色雨云缠绕在山尖,犹如蒙着一层轻纱,神秘而缥缈。
来这之前我做了些功夫,查阅了古堡有关资料,对古堡有了大致的了解。据《塘口志》记载,泰安堡占地6000多平方米,始建于1807年(清嘉庆十一年),由当地刘氏族人刘振槐主持募款兴建。云集无数能工巧匠,花费大量资金,泰安堡历经整整3年才完成主体部分的修建。后由刘子燕牵头出资修整,泰安堡才最终完工。据匡算,每一座塘口古堡的建造都需耗资20万到40万两白银,耗时三四年甚至更长。由此可见,建造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堡,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项浩大工程。
堡内除了住房外,还建有粮仓、水井、厨房、商铺、医疗室、祠堂,各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据悉,堡内一般可住200-500人甚至更多。当然,建造古堡的最终目的并非住人,而是防土匪,因此每一座古堡都是按防范土匪的功用去设计、建造的。
塘口古堡最突出的外墙,是建设者在建造时最下苦心的部分。据介绍,塘口古堡的城墙采用了中国城堡外墙的夯筑方法,即用灰砂夯土夯筑。为了增强城墙夯土黏性,建设者选用细沙、红泥、石灰粉、纸筋和红糖浆作原料,并按照一定的配合比例,混合加工出强度和硬度堪比水泥的黄泥。建造时,筑墙工人会按照墙的厚度,用木板把两边围固。接着把原料倒入板槽内,手持木棍不断舂压,压至墙体坚固为止。随即将板槽加高,如此往复逐层往上建筑。这样建造出来的古堡外墙坚固无比,能够抵御枪炮的攻击,也能承受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侵蚀。
除了在外墙设计和建造上用尽心思,建设者还在兵械设置上下了一番大功夫。
据《塘口志》记载,泰安堡城墙长约73米、宽约84米,墙厚1米、高6米。围墙上端用花岗岩条石铺筑跑道,各向两边伸出1米左右,内外两侧各有砖砌护栏,内矮外高。古堡西南处设有一个大门,这里原来是由两扇古色古香的扫杆木组合而成。大门两边是厚重的石门夹,内设暗道机关,便于打击贼匪。此外,门顶上设有蓄水池,防止来犯者火攻。
泰安堡城墙与宗祠之间,左右各砌有一面墙,分别设拱门通往南北两边的空旷处。而在右边的水井旁,原设有两间房。除此之外,城墙四角原筑有10米高的瞭望炮楼,可惜现已不复存在。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堡内的前后方还有两条通往外面的暗道,供紧急情况使用,但因年代久远,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关于暗道的痕迹了。
我们一行人从大门进入古堡。虽说是大门,但门宽只有1米余,明显与宏大的建筑不相匹配。而门框用巨大的石条紧密镶嵌着,显得十分厚实沉重,据介绍这是为防范土匪进攻而特地设计的。继续深入我们发现,堡内别有洞天。
堡内正中间为刘氏宗祠。宗祠保存得相当完好,其门口两侧各有一棵鸡蛋花树,叶质饱满、翠绿诱人。刘氏宗祠面阔5间,砖木结构,三进院落,两边置耳房,面宽约20米,进深约40米。硬山式镬耳封火山墙,平脊,素瓦当滴水剪边,木雕封檐板,青砖墙,石柱础。宗祠头门设有挡中,上有凹雕“刘氏大宗祠”横额,门额上有五彩雕刻花鸟,栩栩如生,门两侧凹雕对联为“南开三派,泰乙藜光”。深入其中,可以看到二进院落两侧设屏风,地面白泥阶砖,天井两侧设有廊庑。三进院落正中,是供奉刘氏祖宗的牌位。历经岁月的淘沥,现在宗祠内的雕梁画栋墨痕已经褪去,斑驳依稀,只有天井那两株古梅还年年爆出新芽,岁岁芬芳。
泰安堡内除了刘氏宗祠,其他房子或倒塌荒废、或拆除、或被清除,院子里空空落落,只有四周的城墙还保存完整。站在墙下望上去,一排排墙垛高高耸立着,空旷地与四角的天空相对着,似乎在默默地等待一双双探访的脚步。从刘氏宗祠转出来后,沿着阶梯登上城墙,我们发现墙垛上设有许多外窄内宽的枪孔。城墙上每隔两米还有一个小孔洞,墙上四角筑有瞭望台。从城墙上望下去,城外方圆数里的动静一览无遗,远处美丽的塘口河畔绿竹婆娑,连绵不断。
3
塘口古堡建成后,曾经历过多次兵灾贼劫。据史料记载,从前阳春八甲一处名叫“千家洞”(即今仙家洞水库所在地)的山窝有匪屋逾千家。土匪打家劫舍,塘口地区成为其劫掠的主要目标。
最惊险的一次土匪抢劫事件,发生在民国年间。当时,来自阳春的山匪企图洗劫永安堡,但还在堡外一里处,山匪就已遭到堡内车仔炮的猛烈攻击。那炮装满火药、铁砂、犁头铁,还加了铁链、大糠,熊熊燃烧着的大糠和烧红的铁链吓得山匪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敢前来骚扰古堡。此后,随着土匪的逐渐消失,塘口古堡抵御盗贼的作用也渐渐被弱化。
上世纪30年代,当地在古堡内开设学校,供村民子弟读书,泰安堡则改建为横山小学。现在,泰安堡的刘氏宗祠门顶上还刻有“为国育才”4个红色大字。
1940年8月,中共阳江县委安排共产党员廖绍链到阳江县西平乡(今塘口镇)横山小学任校长。利用老师身份作为掩护,他在泰安堡横山建立了阳春县金堡、阳江县横山一带党组织的落脚点。9月,林元熙、庞瑞芳等人又先后被派往横山小学任教,并负责领导阳江西区一带的党组织工作。随后不久,此地建立起金横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横山小学党支部,林元熙任支部书记。
此后,党组织以泰安堡为据点,在当地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扩大党员队伍,加快在农村立足。除此之外,党组织还在当地深入发动群众,办农民识字班,使党组织扎根农村,点燃革命圣火。
随着党组织日益壮大,1949年2月,中共阳江县委和阳江县人民民主政府先后在横山附近的塘口梅花地村成立。随后不久,中共金横区委、中共路北区委、中共路南区委、中共江城区政府、路南区人民民主政府也先后成立,金横区民兵总队、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使古堡又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堡垒。
如今,修葺一新的泰安堡已落实保护措施。旁边还建起一座崭新的红色展馆,用来收存古堡的记忆,供后人凭吊。饱含岁月沧桑、又历经炮火“洗礼”的古堡终于迎来了重生。
古堡的发展历程,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每一个遍布在其身上的或深或浅的弹孔背后,都是一段斗争史;每一段城墙都见证了为了生存而不断抗争,也见证了岁月的辉煌。

 粤公网安备 44172102000122号
粤公网安备 44172102000122号